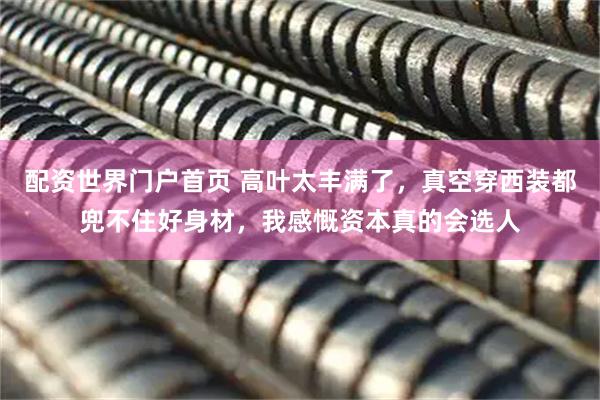引子
你是否曾想过,一场权力的交接,究竟是历史洪流无可阻挡的必然,还是某个瞬间,某个选择,激起的偶然涟漪?
在盛唐那流光溢彩的宏大叙事之下,一个懦弱皇帝的短暂反抗,一声在朝堂上不合时宜的怒吼,是否真的如一颗石子投入大江,仅仅激起了一圈微不足道的波纹,便消散无踪?
不。
那并非石子。那更像是一把钥匙,一把由命运亲手递上的钥匙,开启了一座早已建成的潘多拉魔盒。
这背后,是一场精心策划、潜行数十年的惊天布局。一个女人的野心与一个王朝的命运,早在那个孱弱的太子跪在父亲病榻之前,就已在无人察觉的黑暗中,完成了最后的交易。
唐中宗李显的选择,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无关紧要。
他只是一个祭品,用来祭奠一个旧时代的终结,和一个新纪元的诞生。
01
公元683年,深冬。

东都洛阳,皇城大内,贞观殿。
殿内温暖如春,角落里数座三足金炉,正不知疲倦地吐着来自异域的龙涎香,那浓郁的香气与殿中弥漫的汤药味纠缠在一起,形成一种沉闷而压抑的诡异气息。
病榻之上,大唐的第三位君主,唐高宗李治,正耗尽他生命的最后一点余烬。他的呼吸微弱如游丝,曾经睿智的双眼如今浑浊不堪,费力地转动着,试图看清眼前的一切。
他看到了跪在榻前,身着太子朝服的儿子,李显。
李显的头埋得很低,宽大的袍袖下,紧握的双拳因过度用力而微微颤抖。他能感受到父皇的目光,那目光越过了他的头顶,投向了他身后那一道厚重的珠帘。
帘后,端坐着一个身影,那是帝国的另一位统治者,天后武则天。
她一言不发,但她的存在,便足以让这座宫殿里的空气凝固。所有内侍、宫女、乃至跪在地上的皇子,都屏住了呼吸,仿佛任何一丝声响,都是对那份寂静的亵渎。
「显儿……」
李治的声音嘶哑干涩,仿佛是从一口枯井中艰难地打捞出来。
「儿臣在。」
李显立刻叩首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,不知是悲伤,还是恐惧。
李治没有看他,目光依旧牢牢地锁在那道珠帘上。他与那个女人斗了一辈子,爱了一辈子,也怕了一辈子。如今,他要将这个帝国,连同这个他无法掌控的儿子,一并交到她的手上。
「军国大事……有不决者……」
他喘息着,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与死神角力。
「兼取天后进止。」
这十个字,终于说完了。李治的身体猛地一松,仿佛卸下了千钧重担,眼中的最后一丝光芒,也随之黯淡下去。
贞观殿内,一片死寂。
随即,压抑的哭声响起。
李显伏在地上,身体剧烈地颤抖。父皇的驾崩固然让他悲痛,但那句遗诏,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,在他正式登基之前,就已冰冷地套上了他的脖颈。
他即将继承的,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分割的皇权。一半在龙椅之上,另一半,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道珠帘之后。
他不敢抬头,却能清晰地感觉到,帘后那道平静的目光,正穿透层层珠玉,落在他颤抖的脊背上。那目光没有温度,没有情感,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、令人心悸的威严。
他不知道,这句遗诏,并非托孤,而是一份权力转让的最后确认书。
他更不知道,他父亲的死亡,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而是另一个时代——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母亲的时代,真正意义上的开始。
02
李显的性格,是在恐惧的土壤中长出的藤蔓,懦弱、天真,又带着一丝不切实际的渴望。
他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。在他之前,两位兄长的命运,是他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大哥李弘,仁孝谦和,被立为太子,监国理政,深得朝臣之心。然而,他却在二十三岁的年纪,离奇地“病逝”于合璧宫。宫中私下里都在传,太子是因为在对待萧淑妃女儿的婚嫁问题上,违逆了天后的意思。
二哥李贤,聪慧过人,文采风流,曾注《后汉书》,名满天下。他被立为太子后,却又因一桩“谋反案”被废为庶人,流放巴州。最终,被母亲派去的酷吏丘神绩逼令自尽,年仅二十九岁。
兄长们的悲惨结局,像两座巨大的墓碑,矗立在李显通往东宫的路上。储君之位,就这样戏剧性地、带着血腥味地落到了他的头上。
在东宫的那些年,他活得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。他亲眼见证了母亲如何以皇后之尊,与父皇“二圣临朝”,权势滔天,一步步将帝国的权力纳入掌中。
那些曾经功勋赫赫,足以影响朝局的关陇贵族元老,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……一个接一个,在他母亲雷霆万钧的政治手腕下,或被流放,或被赐死,家族败落,烟消云散。
父皇李治的风眩之症,给了母亲最好的舞台。每当父皇头痛欲裂,无法处理政事时,母亲便会从珠帘后走到台前。她的决断,她的意志,甚至比父皇的圣旨更为迅速,更为有效。
朝臣们渐渐习惯了,在向皇帝奏事的同时,更要揣摩天后的心意。
李显看在眼里,内心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、混杂着崇拜与恐惧的复杂情感。他渴望得到母亲哪怕一丝的认可,却又本能地畏惧她那深不可测的权力和永远无法揣度的内心。
他以为,只要足够顺从,足够恭敬,就能在这风暴的中心,求得一个安稳。
他忘了,对于一个真正的权力猎手而言,顺从的羔羊与待宰的羔羊,唯一的区别,只在于被送上祭坛的时间早晚而已。
他天真地以为,当父皇驾崩,自己坐上那至高无上的龙椅时,就能摆脱这片巨大的阴影。他甚至在内心深处,偷偷梦想着能够像他的祖父,伟大的太宗皇帝一样,建立自己的班底,施展自己的抱负,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。
这种天真,很快,就将让他付出他所能付出的一切作为代价。
03
弘道元年(683年)十二月,李治驾崩于贞观殿。七日后,李显在灵柩前即位,改元嗣圣。
当他第一次身着龙袍,坐上那张象征着天下最高权力的龙椅时,一种前所未有的、虚幻的自由感包围了他。他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文武百官,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权力欲,在这一刻,如同地火般喷涌而出。
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,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。
而证明权力的最好方式,就是人事任免。
他要提拔自己的“自己人”——他的皇后韦氏一族。他的岳父,韦玄贞,时任普州参军,一个微不足道的九品小官。李显要一步将他提拔为豫州刺史,这已经是破格之举。
但他觉得还不够。他要给韦玄贞一个更大的荣耀,一个足以让所有人明白谁才是这个帝国真正主宰的职位。
他要让韦玄貞当侍中。
侍中,门下省的长官,正儿八经的宰相之职,帝国的权力核心。
诏令发出,却在政事堂被卡住了。
中书令裴炎,这位父皇指定的顾命大臣,以一种不容置喙的口吻,当庭驳回了皇帝的任命。理由是:韦玄贞资历不足,且身为外戚,不宜担任宰辅之职。
裴炎的语气平静,却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意味。他看着御座上的年轻皇帝,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敬畏。
李显被彻底激怒了。
那不仅仅是对他皇权的挑战,更是对他作为一个男人,一个皇帝尊严的践踏。长久以来积压的恐惧、压抑、不甘,在这一刻尽数爆发。
他从龙椅上霍然起身,指着裴炎的鼻子,发出了那声震惊朝野的怒吼:
「我以天下给韦玄贞,也无不可,难道还吝啬一个侍中吗?」
这句话,如同一道惊雷,炸响在死寂的朝堂之上。
满朝文武,包括那些刚刚还在窃窃私语的官员,瞬间噤若寒蝉。他们惊愕地看着这位年轻的皇帝,像在看一个完全不懂游戏规则的孩童,正在万丈悬崖的边缘,肆意地表演着他那幼稚的舞蹈。
所有人都心知肚明,裴炎之所以敢于当面顶撞皇帝,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忠心耿耿的社稷之臣,而是因为他的背后,站着那位刚刚成为皇太后的女人。
这句话,也以最快的速度,通过无数双耳朵和嘴巴,传进了武则天的仪鸾殿。
据当时殿内的宫女后来回忆,皇太后听完这句回报,并没有发怒,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。她只是放下了手中的茶盏,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、冰冷的笑意。
她对身边的上官婉儿轻轻说了一句:
「痴儿,他终究还是把刀柄亲自递到了我的手上。」

此时的李显,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愤怒之中,他没有意识到,一张无形的大网,早在他登基之前,就已经织就。他的母亲,通过科举制度,提拔了数以百计出身于寒门庶族的官员。这些人,对铲除他们晋升之路上最大障碍——关陇门阀——的武则天,充满了感激与忠诚。
他们忠于的,不是大唐李氏的血脉,而是那个赐予他们权力、地位和未来的“天后”。
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,早已在不知不觉中,完成了权力的更迭。李唐的根基,已被悄然蛀空。
李显的反抗,幼稚得像一场早已写好结局的独角戏。
04
嗣圣元年(684年)二月。
距离李显登基,仅仅过去了五十五天。
他的皇帝生涯,戛然而止。
武则天没有给他任何辩解、忏悔或是求饶的机会。她直接召集百官于乾元殿,在那个李显曾经接受朝拜的地方,宣布了废黜他的诏书。
诏书中,历数其罪,条条都指向他试图“私授外戚,颠覆社稷”,欲将李唐江山拱手送人。
当羽林军的铁甲卫士冲入李显的寝宫时,他正与韦后商议,如何应对裴炎等人的“不敬”。当那些闪烁着寒光的兵器和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出现在眼前时,他才如梦初醒。
他被粗暴地从锦榻上拉拽起来,那一刻,他透过人群的缝隙,看到了不远处,端坐在殿堂之上的母亲。
她的眼神冰冷如铁,仿佛在看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
「我无罪!」
李显发出了绝望的呼喊。
武则天身边的中官高声回应道:
「陛下欲将天下给予韦玄贞,岂能说无罪?」
李显瞬间语塞,面如死灰。
他被废了。废得如此轻易,如此迅速,仿佛只是被拂去一件龙袍上的灰尘。
他被废为庐陵王,他的妻子韦氏被废为庐陵王妃。他们被押上囚车,连夜送出神都洛阳,流放至偏远的房州。
而他的弟弟,性格温顺谦恭的豫王李旦,被扶上了皇位,成为新的傀儡,史称唐睿宗。李旦甚至比他更惨,他被彻底软禁在宫中,连朝臣都无法轻易见到,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“囚徒皇帝”。
囚车颠簸,驶出洛阳厚重的城门。寒风凛冽,吹透了李显身上那件单薄的囚衣。他回头望着那巍峨的城墙,在视野中越来越远,直至化为一个黑点。
他终于明白,自己那句脱口而出的气话,不过是母亲早已准备好的剧本中,一个恰到好处的、用来拉开大幕的借口。
就算他什么都不做,就算他像弟弟李旦一样,做一个温顺听话的木偶,结果也不会有任何不同。
武则天需要的,从来都不是一个听话的儿子。
她需要的,是一个空出来的、可以任由她掌控的皇位。
这,仅仅是开始。
一场更大的风暴,正在帝国的东南方酝酿。
同年九月,开国元勋英国公李绩的孙子,柳州司马徐敬业,在扬州起兵,发布了一篇由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骆宾王亲笔撰写的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。
“伪临朝武氏者,人非温顺,地实寒微……包藏祸心,窃窥神器……”
“入门见嫉,蛾眉不肯让人;掩袖工谗,狐媚偏能惑主。”
这篇檄文,文采飞扬,辞藻华丽,将武则天的“罪行”昭告天下。檄文传至洛阳,就连武则天本人读后,也不禁赞叹其才华,惋惜道:“宰相安得失此人!”
然而,赞叹归赞叹,她的手段却无比冷酷。
她迅速调集三十万大军,由大将李孝逸率领,前往镇压。
而远在房州的李显,当他听到叛军打着“匡扶庐舍王”的旗号时,非但没有感到一丝希望,反而陷入了更深的、无边无际的恐惧之中。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母亲的性格。这只会成为她大开杀戒的最好理由,加速她对整个李唐宗室的清洗。
果然,徐敬业的叛乱,不到三个月便被轻易平定。
随后,武则天借此为由,在帝国内部掀起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政治清洗。
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人,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。他们在洛阳设立了专门的推事院,人称“新开门”,凡是进入此门的,无一生还。他们发明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,如“定百脉”、“喘不得”、“突地吼”等等,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被怀疑对武则天不忠的李唐宗室和朝中元老。
一时间,神都洛阳血雨腥风,人人自危。告密之风盛行,儿子揭发父亲,妻子状告丈夫,无数的冤案,将李唐的宗亲、功臣后裔,成批地送上了断头台。
武则天用铁与血,用最极致的恐怖,一点点清除着她通往权力之巅道路上的所有障碍。
在房州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,李显度日如年。每一次,当他听到门外传来京城口音的官话时,都会立刻面无人色,以为是母亲赐死的诏书到了。
他不止一次地想要解下腰带,悬梁自尽,以求一个了断。
每一次,都是他的妻子韦氏,死死地抱住他,流着泪哭喊道:
「祸福无常,何必如此轻生!人生在世,总有活路,岂有必死之理?」
在这不见天日的十四年流放岁月里,这对患难夫妻,成了彼此唯一的精神依靠。
而远在神都洛阳的武则天,则在等待。
她似乎在等待一个信号,一个足以让她打破千年传统,正式登上权力之巅的、来自上天的启示。
05
就在李唐宗室的鲜血,几乎要染红洛水之时,武则天的侄子,时任宰相的武承嗣,从并州送来了一份八百里加急的密报。
密报中并非军情,而是一块在洛水中打捞上来的白色石头。
石头之上,赫然刻着几个形似符篆的神秘字符。
武则天立刻下令,将这块石头奉入宫中,并召集了天下所有博学之士、高僧、道长,试图破解这“天降”的谜团。
然而,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那些字符,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文字。
就在武则天渐渐失去耐心,认为这不过是一场闹剧之时,一个意想不到的人,站了出来。
他就是深受武则天宠信的白马寺主持,薛怀义。
这个原名冯小宝的市井无赖,因其特殊的身份,得以近距离观察这块奇石。他跪在武则天面前,以一种无比虔诚和激动的语气,宣布自己破解了天神的旨意。
他颤抖地解读出的那句话,让整个宫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「圣母临人,永昌帝业。」
圣母,临于万民之上,她的帝业,将永远昌盛。
这八个字,如同一道神谕,瞬间击中了所有人的内心。它赋予了武则天梦寐以求的东西——天命。
这块被迅速命名为“宝图”的祥瑞,被以最隆重的方式昭告天下。紧接着,仿佛是连锁反应一般,各地的祥瑞纷至沓来。

有人说在洛阳城南,看见五彩凤凰盘旋于宫殿上空,三日不散。
有人说在嵩山之巅,挖出了一块刻有“武”字的巨大龟甲。
更重要的是,武承嗣等人,指使十个胡僧,编纂了一部《大云经疏》。他们借用佛经中“净光天女”的故事,进行引申和阐述,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:皇太后武则天,乃是弥勒佛转世,应当取代李唐,成为人间君主。
一部部崭新的经书,被迅速刊印,分发至全国各地的寺庙。一时间,天下僧侣,都在向信徒们宣讲着“女主当国”的合法性与神圣性。
一场声势浩大的、精心策划的舆论运动,席卷了整个帝国。从朝堂到乡野,从贵族到平民,所有人都在谈论着“天命在武”。
李显的反抗与否,徐敬业的仓促起兵,在这样周密得令人窒息的“天命”布局面前,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,甚至有些可笑。
武则天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。
她要的,是名正言顺的皇位。
她要成为皇帝。
06
朝堂之上,最后的博弈,或者说,最后的表演开始了。
那些在酷吏政治下幸存下来的李唐旧臣们,面对这股由“天意”和“民心”汇聚而成的滔天洪流,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与无力。
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。
宰相裴炎,当初那个亲手将李显拉下皇位的顾命大臣,在徐敬业起兵之初,曾私下对人说:“太后若能还政于皇帝,则反贼不讨自平。”
这句话,被迅速告密。
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,立刻将这位曾经的功臣投入大牢,最终以谋反罪处斩。
她用裴炎的血,给所有人上了最后一课: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
随后,她开始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。她下令将都城从长安彻底迁至洛阳,并改名为“神都”,从地理和心理上,彻底摆脱李唐王朝旧都的政治影响。
她在朝堂上设立铜匦,分为“延恩”、“伸冤”、“招谏”、“通玄”四格,鼓励天下人告密。一时间,无数人通过告密,一夜之间飞黄腾达,也让无数家庭,瞬间家破人亡。
她又亲自开创了“殿试”和“武举”。在科举的最后一关,由她亲自面试,决定名次。这彻底打破了士族门阀对官位的垄断,让更多寒门子弟得以进入权力中枢。
这些通过新制度上来的官员,自然将武则天视为唯一的恩主和效忠的对象。
她的每一步,都在瓦解着李唐王朝数百年来建立的统治根基,同时,又在建立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、全新的、坚不可摧的权力结构。
这是一个阳谋。
一个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,却无力阻止的宏大计划。
最后,由她的侄子武承嗣、武三思领头,百官、宗室、地方官吏、乃至四夷首领,数万人联名上书,请求皇太后顺应天意,登基称帝。
这是一场盛大的政治劝进。
武则天按照惯例,先是“义正辞严”地拒绝,表示自己不能对不起先帝。
百官再请。
她再次拒绝。
如此三请三辞之后,她才终于“勉为其难”地表示,既然天意如此,民心所向,她也只能“顺应天命”。
所有流程,都已走完。
万事俱备。
07
公元690年,天授元年,九月初九,重阳佳节。
神都洛阳,则天门。
这一天,六十七岁的武则天,身着前所未有的、绣有日月星辰的皇帝衮服,头戴十二旒的帝王冠冕,在万众瞩目之下,缓缓登上了则天门的城楼。
城楼之下,是黑压压的人群,文武百官,诸国使臣,平民百姓,数十万人,鸦雀无声。
她站在城楼之巅,俯瞰着脚下的万里江山和芸芸众生。从一个十四岁的才人,到如今的帝国主宰,她走了整整五十三年。
这一路,充满了鲜血、阴谋、背叛与杀戮。
但她,终究是走到了权力的最顶峰。
“改唐为周,朕为圣神皇帝。”
她的声音,通过内侍的层层传达,响彻云霄。
城楼之下,山呼万岁之声,排山倒海,直冲云霄。
中国历史上,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帝,就此诞生。
那一刻,远在千里之外的房州,李显或许正透过茅屋的破窗,望着北方阴沉的天空。他不会知道神都正在发生什么,但他十四年的流放生涯,早已让他彻底明白了权力的真谛。
他不再是那个会因为一句话而被激怒的年轻皇帝,岁月和苦难,磨平了他所有的棱角,也教会了他最重要的一课:隐忍。
他的母亲,那位高高在上的女皇,在位十五年,将大周王朝的统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她知人善任,提拔了狄仁杰、姚崇、宋璟等一代名相;她重视农业,改革吏治,使得国家在她治下,依旧保持着强盛的国力。
史书亦无法抹杀她的功绩,称其有“贞观遗风”。
然而,当她步入晚年,当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时,一个最根本的问题,摆在了她的面前:
谁来继承这个庞大的帝国?
是她的侄子,武承嗣、武三思?还是她的儿子,李显、李旦?
血缘亲情,这个曾被她一度视为权力障碍的东西,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,终究还是战胜了冷酷的政治考量。
在宰相狄仁杰等大臣“陛下立子,则千秋万岁后,配食太庙,承继无穷;立侄,则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”的反复劝说下,她那颗坚硬了一生的心,终于动摇了。
“姑侄与母子,哪个更亲?”
狄仁杰的这句话,击中了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圣历元年(698年),在被流放了整整十四年后,李显被一纸密诏,悄悄地召回了神都洛阳。
当他再次见到母亲时,她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而他,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。
母子二人,相对无言,唯有泪千行。
历史,在这里,开了一个巨大而又宿命般的玩笑。
08
多年以后,神龙元年(705年)。
一场由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的宫廷政变,结束了武周的统治。病榻上的武则天,被迫将皇位传还给太子李显。
大唐,复国。
重新坐上龙椅的李显,已是四十九岁。他看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宫殿,看着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,心中百感交集。
他没有对母亲进行任何形式的清算,反而给了她“则天大圣皇帝”的尊号。他知道,自己能够复位,并非因为自己有多么贤明神武,仅仅是因为,他是她的儿子。
他的一生,仿佛就是为了印证母亲的强大而存在。
他的第一次被废,为母亲临朝称制铺平了道路;他“匡扶对象”的身份,为母亲清洗政敌提供了最好的借口;他的最终复位,则让母亲的王朝,得以用一种最和平、最体面的方式,回归李唐的轨道。
他的人生,就像一个完美的闭环,起点和终点,都是由他母亲的意志所决定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从不因某个人的意志而停留。武则天称帝,是那个时代权力斗争的终极产物,是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,更是她个人超凡的智慧、野心和冷酷无情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。
那么,回到最初的问题。
李显当年在朝堂上的那句气话,那次短暂而幼稚的反抗,真的重要吗?
或许,它唯一的意义,就是让那场早已注定要发生的权力更迭,进行得更加顺理成章,也更加富有戏剧性罢了。
在历史的长河中,他不过是那艘名为“武周”的巨轮,在劈波斩浪、驶向权力彼岸时,船舷边被溅起的一朵,无足轻重的浪花。
驰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